
黄鹏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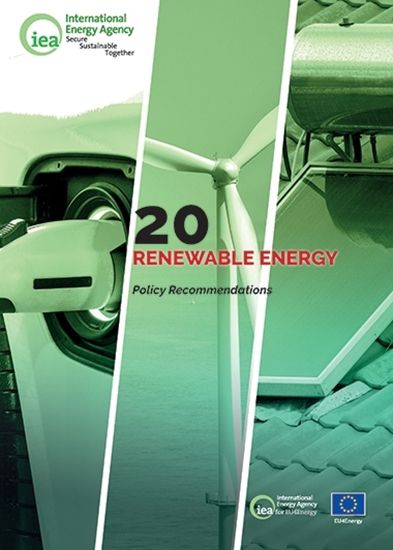
(图片来源:国际能源署官网)
2019年世界能源投资年度报告指出,上游石油和天然气的基建和开采项目支出在2018年增加4%,钻探煤炭新来源的投资首次上升2%,而全球对新再生能源投资的规模却放缓约2%。国际能源署(IEA)称,全球必须在2030年前加倍注资再生能源并同时削减石油和煤炭投资,才有望实现《巴黎协定》下各国承诺对控制平均气温所设的目标。因此,构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法治体系是推进能源消费转型,进而实现《协定》目标的必经之路。
一、可再生能源法治建设助力实现《巴黎协定》目标
国际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如今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诸多国家的不懈努力下,人类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协定》是继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形成2020年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措施与制度的一致共识。
《协定》明确提出“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 ℃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 ℃之内”的目标,同时制定了“只进不退”的棘齿锁定机制(Ratchet),要求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目标建立在不断进步的基础上,并且自2023年后每五年对各国自主贡献目标的落实情况进行定期评估。这些数字目标和机制的背后表明了国际社会推动世界低碳发展的决心,因此《协定》的生效必将对世界经济发展、能源消费、环境治理、金融机制、技术创新等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俊峰,柴麒敏,2017)。其中,就能源消费而言,由于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80%的二氧化碳主要源自化石燃料的燃烧(戴维•M.德瑞森,2015),《协定》必将引起原以石油和煤炭为主的高碳排放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
近年来,随着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物理特性和资源赋存特性的逐步了解,其已成为各国发展低碳经济中的“香饽饽”。然而,由于可再生能源存在不稳定性、生产价格高、利用率相对较低等问题,现阶段各国也正面临着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诸多挑战。在各种应对挑战的措施中,由于法律所具备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加强可再生能源法治建设成为绝大多数国家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质量的共同选择。因此,构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法治体系是推进能源消费转型,进而实现《协定》目标的必经之路。
二、中国可再生能源法治建设已步入正轨
中国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世界经济、政治大国,除了继续坚持发达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承担历史责任外,还呼吁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协定》的达成、签署、批准和生效的全过程中,中国做出了关键性贡献。与此同时,为达成《协定》所设定的低碳发展目标,中国积极推进能源改革,不仅主动提出国家自主贡献(NDC)减排目标,即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提升到20%左右(莫建雷等,2018),而且通过加强可再生能源法治体系建设等途径对能源产业进行规制和调整,切实履行了减排义务。
现阶段,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础、大量可再生能源政策为主干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有机体系(李艳芳等,2015)。这些可再生能源政策与法律相辅相成,保障了可再生能源科学、合理、安全和高效的开发利用。一方面,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能源发展五年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长期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五年规划,以及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和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专项规划。根据具体规划中所明确的目标和原则,可再生能源有关主管部门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实施细则。此外,地方政府及能源主管部门也根据国家发展规划的要求陆续制定了配套的地方规划,以推动各自管辖区域内可再生能源发展,落实国家政策要求(于文轩等,2019)。另一方面,中国基于《可再生能源法》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相关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地方性立法的司法实践,确立了一套对发展可再生能源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分类电价制度和财税支持制度等。具体而言,总量目标制度要求在总的能源消费或电力消费中必须有规定比例的能源或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李俊峰,王仲颖,2005)。国家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通过制定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目标和采取相应措施,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要求电网企业应对电网覆盖范围内符合并网技术标准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生产的电力优先调度,并全额予以收购。由于可再生能源供应的电量存在着间歇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电网企业通常从安全、效益的角度出发,天然地排斥可再生能源电力入网,实施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有助于缓解“上网难”问题,进一步减少电力供应商投资风险、降低可再生能源项目交易成本、缩短项目准入时间、提高项目融资的信誉度等。分类电价制度,是指根据不同技术种类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特点,按照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在某一时期内分门别类地制定相应的上网电价或招标电价的制度(李俊峰,王仲颖,2005)。完善的分类电价制度,能够使市场主体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开发利用不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回报大体相同(毛如柏,安建,2005),从而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商的利益预期。财税支持制度主要包括税收优惠和贷款支持两方面,一是通过降低税率、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措施,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领域(王书生,赵浩君,2007);二是通过开征新税种、提高税率、取消税收优惠等措施提高非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价格,促进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生产、供给与消费。
总体而言,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无论是在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上,还是在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上,都已初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可以说,中国可再生能源法治建设已步入正轨。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法治建设应加速与世界接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离不开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因此国际合作是完成《协议》目标的基础。就能源消费而言,要想高效地达成《协定》所强调的能力建设、资金和技术转让等多方面的国际合作,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可再生能源法治体系刻不容缓。
目前,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等都已基本建成较为完备的可再生能源法治体系。具体而言,美国十分重视立法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其可再生能源立法最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可再生能源法治建设过程中,美国综合运用了综合性法案、单一法案、专门法案等手段,从联邦和州两个层次进行立法。在联邦层次,形成了以《1978国家能源法》《1992国家能源政策法》和《2005能源政策法》为基本框架的联邦能源政策立法体系;在州层次,大多数州都通过了相应的可再生能源立法,并都有相应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李艳芳等,2015)。就特点而言,美国可再生能源立法注重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具有因地制宜的特点,同时还确立了财政刺激手段和直接管制手段,尤其注重财政刺激手段。德国迫于能源资源紧缺的压力,很早就开始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并也同样重视可再生能源法治建设,早在1974年就颁布了能源发展框架项目。目前德国已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核心,其他相关立法为配套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就特点而言,德国可再生能源立法强调了理性的制度建构,一是强调法律背后的科学依据,缓解了法律条文和现实之间的脱离问题;二是强调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平衡了可再生能源和传统化石能源间的价格差距;三是明确规定了如行政主管部门、发电装置运营方、电网运营商等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便将能源战略的重点定位于能源多元化,并十分看重可再生能源立法。截止目前日本已颁布了《替代石油能源法》《促进新能源利用的特别措施法》《独立行政法人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法》《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等多部针对可再生能源的专门性立法,就特点而言,日本可再生能源立法强调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管理,且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如许可义务、政府可再生能源利用义务以及电力事业者可再生能源利用义务等,同时还注重落实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经济刺激措施(李响等,2016)。
通过与上述发达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法治建设情况进行比对,应当看到,尽管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现阶段中国可再生能源法治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需要(李艳芳,2010),要想与世界接轨仍旧任重道远。为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加快与国际接轨进度,中国应结合可再生能源开发、加工、转换、储存、运输、供应、利用、贸易和管理的特点和实践,进一步加强可再生能源法治建设。而当下健全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体系是中国完善可再生能源法治建设最为关键的一步。具体而言,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加强对监管机制、评估机制、考核机制的完善,对重要的管理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其次,要健全专项立法,针对不同的可再生能源类别、开发利用技术特点和条件以及地域禀赋等资源的个性特征,制定可再生能源专门领域立法(肖国兴,叶荣泗,2010),并在进一步立法中着重规定投资补贴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明确一定条件下的价格和财税激励措施,鼓励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最后,要完善配套规章,特别是应尽快制定《可再生能源法》授权国务院制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的具体办法、电网企业优先调度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具体办法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项目税收优惠办法。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2017级博士生)
参考文献:
[1] 俊峰,柴麒敏.《巴黎协定》生效的意义[J].世界环境,2017(1).
[2] [美]戴维•M.德瑞森.法律的动态经济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3] 莫建雷等.《巴黎协定》中中国能源和气候政策目标:综合评估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18(9).
[4] 李艳芳等.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法律与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5] 于文轩等.可再生能源政策与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6] 李俊峰,王仲颖.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解读[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7] 毛如柏,安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8] 王书生,赵浩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探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7(2).
[9] 李响等.能源法学[M].山西: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
[10] 李艳芳.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中国可再生能源法制[J].政治与法律,2010(3).
[11] 肖国兴,叶荣泗.中国能源法研究报告2009[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Meet the Paris climate treaty temperature targets by enhancing renewable energy legislative construction
HUANG Penghui
On May 15, 2019,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Paris AFP, the earth’s atmosphere likely contains more carbon dioxide today than at any time in at least 3 million years. EIA’s 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9 pointed out that the expenditures on growing oil and natural gas project has increased by 4% in 2018, and the investments in drilling and mining practices has increased by 2% for the first time. However, global investments in new renewable energy has slowed down by 2%. IEA said that the world must double spending on renewable power and slash investment in oil and coal by 2030 to keep the Paris climate treaty temperature targets in play. The renewable energy legislative construction is the key way to promote the energy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Treaty of Paris.
Copyright 2016-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QY-千亿(球友会)官方网站 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